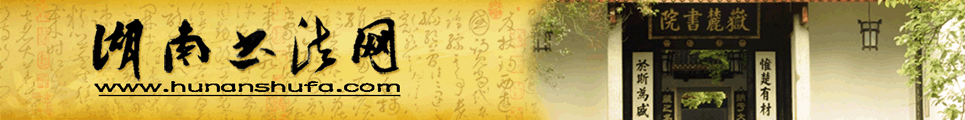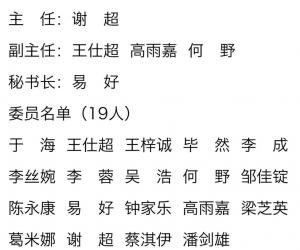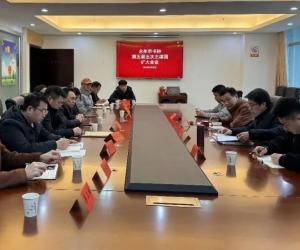刍议书法美学 段新星
刍议书法美学
段新星
摘要:以汉字的书写为载体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这些抽象的线条和符号经过长期的“积淀”过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1)。书法之线关乎人的心灵,并以其独立的美学性格,包蕴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中国书法的发展史是人性不断觉醒、生命力不断弘扬的历史。
关键词:书法;线;生命意识
在世界民族的艺术史上,有许多艺术品种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并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它们在最根本的特点上是共同或相通的,从而形成了世界共同的艺术品种或艺术门类。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都属此类。另外也有一些艺术品种则为个别或少数国家、民族所特有。书法艺术,就是此类中最突出的一例。
书法艺术在我国各艺术门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雕刻与绘画并称;而在中国,总以“书画”相称。书法形式作为华夏民族审美精神的外化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苏轼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真卿,画至吴道子,而尽天下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可见书法的精神内涵和诗、文、画是相等的。书法呈现在具体世界中,不但“同自然之妙有”,而且“达其情性,形其哀乐”(3),“书之为功,同流天地,冀卫教经者也”(4)。书法在点线飞舞、墨色枯润中包蕴着极丰厚的文化精神和哲学境界。
“囊括万殊,裁成一相”(5)
书法是线的艺术,其艺术内容不是“字”以及“字义”的阅读,而是对“字”的线条化和相关形式表现的审美感知。书法通过丰富的用笔,如提、按、顿、挫等手段呈现出线条的浓淡、枯润、长短,体现一种超越于言象之上的玄妙之意和幽深心理。近代法国大雕刻家罗丹曾经对德国女画家萝斯蒂兹说:“一个规定的线(文)通贯着大宇宙,赋予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他们在这线里面运行着,而自觉着自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的。希腊人因此深入地研究了自然,他们的完美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从一个抽象的‘理念’来的。人的身体是一座庙宇,具有神样的诸形式。”(6)又说:“表现在一胸像造形里的要务,是寻找那特征的线纹。低能的艺术家很少具有这胆量单独的强调出那要紧的线,这需要一种决断力,像仅有少数人才能具有的那样。”(7)书法的线正是这样一根“通贯着大宇宙”的“线”;中国书法正是因为书家独到的“决断力”,合乎法度的挥洒“自由”,是主体的审美观照。
中国书法的线有其独特的审美效果,这与简单的几何学线条划分了界线,也奠定了书法在世界艺术中的独特地位。毛笔是中国特有的书写工具,体圆锋尖,刚柔相济,富有弹性。用它创作的书法作品之艺术水准,足以并肩于绘画。中国人把“书画”并称,即充分认识了此点。从书法线条所表现出来的气、力、韵、神亦可窥见一斑。王憎虔就极注重笔力,他说:“张艺、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唯见笔力惊绝耳。”(8)书法也讲究节奏。“书法与诗的节奏有通感,石鼓文开首几行字形的‘大小小大大小,小小大小小大,大小小大大小,大大小小大大’很容易使入联想到平压音韵,而行草书节奏的回环映照就更与诗暗合了。”(9)再举一例:林散之1965年所作毛泽东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据
线条对空间的分割则产生结构和章法,这又进一步扩展和加强了线条的表现力。汉字的形体美,首先表现在字形的图象上。汉字起源于表形性极强的象形字,可以直接表意,因而具有一种“感性显现”的审美基因,能够“形入心通”。其次,在构造上具有匀称、和谐、对称、参差统一等一般形式美规律。汉字形体美在构成上的形式美规律是在汉字方块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汉字的方块化对书法的意义在于:“a.既赋予每一个象形字具有得以自由驰骋的广阔空间,又使它们各自独立,可以随时服从调遣。每一个汉字既是一个‘独立王国’,又只是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b.它使汉字立体化,即使每一个字都有上下左右的立体方位,笔画无论繁简都得有一个结构上的平衡、和谐,都得立得起,都得讲究动态中的中和之美。”(11)
书法艺术中的章法,集字成行,集行成篇,要求一气呵成,“首字统领”,左右顾盼,疏密错落,浓淡适宜。正如邓石如所言:“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故书家当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便是成功章法的典范。
“书,心画也。”(12)书法其实是人的心电图,是人的心灵的潜语,是中国哲学的行为性存在,是诗意的外化形式。它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书家的创作可以说是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与喧泄。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果说自由是人性的规律(现象),那么审美情感是体现人性的情感,是一种自由情感,它更能体现人性及更深层次的人的本质的个人自由。作品便是书家独特人格的流露和生命感的延续。如王羲之的风流遒丽,欧阳询奇峻险绝,郑板桥的乱石铺街等。也有书论把书法作品看作是有生命的形体。
中国书法重视线条,但一个伟大的书家追求的是忘掉线条,从线条中解放出来,以表现书家的心情境遇之悲喜怒忧,展露其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或失序。书法作为线的艺术,其生命力不会减退,只可能在艺术嬗变过程中从人性的觉醒、个性的张扬,走向心灵选择的自由的内在轨迹,从而进一步加强艺术审美功能。
“趣舍万殊,静躁不同”(15)
书法这一线的艺术,它在本质上表现为生命意识的流动。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不等于生命意识的产生。生命意识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范畴。它的产生伴随着一种自我感,即自觉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认同。它的产生又构成了入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动物只有单一实体存在,但并无自我感存在;只有人才有自我,但自我并不是一种静态存在的实体。这种自我感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才产生出来的,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书法中流动的生命意识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表现出那个时代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作为造型艺术的书法显然也不例外。清梁●在《评书帖》中便提出了“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论断。由此我们可以寻找到一种生命意识与历史的统一。
魏晋之世在我国的政治史上无疑是黑暗的。然而,一统社会的瓦解,社会共性的离析,促成了个性的相对发展。这也使得他在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他们在那种荡动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是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艺术,都持有大胆的独立的见解。”(16)这一时期的思潮呈现出由务实转向祟虚,由客体转向主体,由群体转向个体之势。门阀世族之间的权利争夺表现出政治的残酷,使一些失势的门阀贵族和广大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界的希望完全消灭,走上了脱离政治的道路,转而祟尚玄学清谈、祟尚佛学,由积极的救世的人生观趋于消极的避世的人生观。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和探寻亦成为他们逃避现实、慰藉精神的一种途径。这一时代出现的“人性的觉醒”(17)使得它无论在学术的研究上,文艺的创作上或是人生的伦理道德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解放与自由。于是,一种纯粹的“尚韵”的艺术形式伴随着玄学和佛学的思辩与理性色彩被孕育出来了。魏晋成为我国书法艺术最繁荣、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已成为一种必然。晋人书法,以“韵”字为追求的目标。这正是因为当时流行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玄学尚无,无则超旷空灵。当时盛行清谈,由哲学命题转向艺术境界,其理想就是“澄怀观道”(18)“超以象外”(19)。在书法艺术上则表现为潇洒、飘逸、变幻莫测……。梁●以“晋尚韵”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书法趣向是有道理的。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书法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代。书法(主要是楷书)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代长期实践以后,在写法上须进一步规范化,找出其中规律。正遇唐代社会稳定、国力强盛,各种事情都步入正规。故产生了以“尚法”为主旨的书法思潮和艺术实践。唐代许多书家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格遂良、薛程。尤其是欧阳询,字的结构已到了十分精严的程度。盛、中唐之际的大家是颜真卿,晚唐有柳公权。“唐尚法”毋庸置疑取得了极大成功。然而,在唐代这个一统的封建社会里,帝王的绝对权威压倒一切,并成为社会的共性。在这种社会里,入的个性是很难得到自由发展的,往往要以其个性服从社会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便是社会对个性或是生命意识的一种滞固。因此,从艺术本身来看,“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入之失也”,“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南宋姜夔《续书谱》)。唐代的书法是逊于魏晋的。从它在整个书法史的地位来看,它只能是一个“黄金时代”’惟魏晋之世才能称之为“我国书法艺术最繁荣、成就最辉煌的时期”。谈唐代书法,不能不谈孙过庭、张旭、怀素等几位草书大家。其中以张旭为代表,他们在唐人“尚法”的樊篱之外,率先树起了“非法”的旗帜,真正是纯艺术性而非实用性的创作。这为宋人的“尚意”创造了条件。
宋入“尚意”是相对于唐入的“尚法”而言的。“尚法”是祟尚法度,而“尚意”则是强调借书法来抒情达意。从理论上讲,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辨证统一,那么作为抽象符号的书法艺术:它所再现和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尽管汉字属于象形文字,但随着符号的演变,高度抽象的文字越来越不反映任何实际的生活内容,它要再现的只是标准字体的间架结构而已。而书法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又不能仅仅反映标准的符号信息。它恰恰要在艺术线条与文字符号的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主观表现的可能性。因此,如果说唐人“尚法”,强调的是书法艺术的“再现”内容;那么宋书“尚意”,则强调的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内容。关于“尚意”,明人项穆有一种阐述,他说:“书之心,主张布算,想象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风采,笔随意发,即形之心也。”(《书法雅言》)所谓“意在笔端”、“笔随意发”,所强调的就是书法创作时的尚意宣情。通观宋代的书法,以行草书为主流,自由地表达感情和意趣,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风尚。
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为了保住江山,在吸取唐王朝灭亡的教训的同时,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采用科举制度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入仕为官。大量的文人进入官僚机构后一方面导致队伍的庞大,而另一方面促成了包括书法在内的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其二,在北宋中前期,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尚意”的书法创作理念,就是在这种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张扬自己的个性和表达自己的意愿的环境下形成的。
另外,宋人重义理。“所谓重义理,是要求把握到句子所包含的内容,体验古人的基本精神,像陆象山所谓‘先立于其大者’,朱熹所谓‘一旦豁然贯通’,都是说若能把握到这中心思想,那么‘六经皆我注脚’,否则一切学问都只是支离破碎的知识。”(20)古人已往,活着的是我,受用者是我,最后的标准在我,如陆象山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表现在书法上,便是不摹仿古人,力求凭自己的美感经验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宋人对唐人的重法是持批判态度的。米芾特命名他的书斋为“宝晋斋”,意为赞赏晋人的潇洒飘逸。苏拭亦提出了“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口号,黄庭坚也说:“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21)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作书并非真是无法,只是相对于唐代重法而他们重个人表现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可以说,末代亦是一个强调“个人”的时代。
纵观书法艺术的发展史,生命意识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范畴。一个强调“社会(群体)”的时代(如唐代),是一个创作主体生命意识受到滞固的时代;反之,一个强调“个人”的时代(如魏晋、宋代)是一个创作主体生命意识勃发的时代。真正的书法艺术只属于那个“生命意识勃发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发展史是人性不断觉醒、不断弘扬生命力的历史。人通过审美和书艺实践,在发展着的社会关系中不断扬弃自身的历史形态而完善自身。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同人性一道发展,同样长久。
“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书法是心灵的艺术,是书法家心灵的直接表现。它是集体的,因为它表现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它又是个人的,是个体生命意识的流动。西汉扬雄便提出了“书,心画也。”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评论张旭草书时说: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送高闲上人序》)
意思是,“草圣”张旭能将他心中的喜怒哀乐以及看到外物后所引发的各种情感用草书表现出来,所以他的字才变得内容丰富、变幻莫测。因此,书法创作又是书法家将思想、情感外化到作品上的生命意识流动过程。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作为生命意识流动的不同方式,成了美与艺术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动力。关于创作时这些不同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动的,所谓“有动于心”;一类是平静的,所谓“绝虑凝神”。
文坛上,李白饮酒作诗早已传为佳话。“酒之比于别物更有助于文学,也如吸烟在早己知道吸烟之术的地方一般,能有助于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极持久的效果。”(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饮酒之乐在于似醉非醉之时,此时亦是生命意识勃发之际。放眼书坛,因与酒结缘而妙笔生花的亦不是少数。东晋的王羲之素有“书圣”的赞誉。他最为后人称道的作品是《兰亭序》。据文献记载,公元353年
唐代的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草圣”由此而得名。这种彻底地、充分地表露个人内心世界的企图成为后世许多书法家的终极理想。张旭生性嗜酒。他与酒的关系很像李白和酒的关系。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同诗里描写张旭的句子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新唐书》把他的事迹附在《李白传》后,写道:“……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即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故人称“张颠”。唐文宗曾下诏把他的字,李白的诗,斐曼的剑合称“世之三绝”。与“颠张”齐名的还有“狂素”。怀素是一个僧人,但亦嗜酒如命,一日九醉,人称“醉僧”。每当酒酣兴发,遇寺壁庙墙,衣裳器皿,无不书写,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24)。著名的《自序帖》长达700余字,首尾贯通,体势飞动,显示了他精湛的功力和创造性的品格。李白也曾给予热情洋溢的礼赞:“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吾师醉后倚胡床,须臾抹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25)
王、张、怀等书家醉后的创作,显示的是生命在酣醉时的样态,意识、潜意识、情感、想象都纷然织成不可预测的韵律。书法作品也便成了生命意识在艺术世界的一种诠释。书家们把醉当作生命的高潮、生命的提升,把酩酊的状态认为是生命最炽热、最酣欢、最具创造力的状态。这时候,理性的控制和拘谨丧失了,潜意识中所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基层的,得到畅然的吐泄。这个时候不再有所畏惧、惶恐和压抑,有的只是兴奋、自由和“忘我”,“社会”这张无形的“网”已不撕而破。沉浸在其中的只有书家自我精神的大解放、大活跃。生命意识也由此得到最大程度的表现。正因为如此,王、张、怀等才成为大家为世人所推崇,其书作亦被今人奉为墨宝。
酒能助兴,兴之所至,也是大作出炉之时。然而哀之所至呢?“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便作于一种悲愤的心情之下。在“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中,颜氏家族立下了不朽的战功,有三十多人为叛军所害。对这样的忠臣烈士,作为一国宰相的杨国忠却否认事实,一无所表。三年后,颜真卿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面奏皇上,以陈其实,才使死难的颜家烈士平反。此时此刻,为追祭以身殉国的侄子颜季明而写下了这篇祭文。在这样十分的悲痛、无限的哀思、强烈的愤慨之心情下,他无心顾忌笔墨线条、章法布局,唯一考虑的就是文字内容。从书作中线条的粗细分明可以察觉到书写时的时缓时急。然而激动的心情又免不了使字一错再错,他圈了又写,写了又圈。整篇文稿虽姿态离奇、点画狼藉,却浑然一体,气韵生动,不可复得。它不是上书用的奏章,也不是出示的展件,仅仅是无意作书的成果。也正因为这种“无意”而为,圈圈画画与祭文内容结合在一起,使颜真卿坦露得最真诚,表现得最自然。正如张曼所评价的:“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
“兴”、“悲”、“愤”等都属于激动的一类,“静”却是生命意识流动的另一种类型,为书家们创作时所追求的境界之一。虞世南有一段书论千古传诵:“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还,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笔髓论·契妙》)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创作场景:作者掩上书房门,沐手焚香,闭目静坐,如此悄然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舒臂援笔,濡墨再三,然后下笔。蔡邕也言:“夫书,先默坐静思,随应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笔记》)王羲之则主张“凡书贵乎沉静”。‘2‘’欧阳询在《八诀》中也说:“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这些“静”决非动作上的静止,它是超越了思维环境和思维氛围的某种局限、诱惑,赢得心灵自由的一种手段,从而使心灵逐渐排除理性的拘束,达到一种“静照”。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说:“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既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而“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又可理解为生命意识的流动。
元代书法家陈绎曾在《翰林要诀·变法》中说:“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亦有浅深,变化无穷。”这些都属于生命意识流动的不同方式即不同的创作心境给创作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喜怒哀乐的“有动于心”,抑或是“默坐静思”的“绝虑凝神”,它们只是生命意识表现方式的不同而己。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便是书法创作本身心灵的解放。它们以情感为中介走出我的自我,与大自然、与他人、与“人的世界”即人类这个“大我”结为一体,而进入所谓“忘我的境界”。“忘我”并非“无我”,而是“我”的自由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愈是“无我之境”,也愈是有我。
综上所述,书法是一种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指心性的艺术,在意象的抽象线条中展现出自我的胸怀襟抱。书法之线关乎人的心灵,使人生在书艺之中成为诗意的人生。“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刘熙载《艺概》)生命是自由的不断展开的过程,而书法是生命意识流动的载体。书法通过点线的律动,成为揭示精神世界的“有意味的形式”。书法艺术不断开启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人的审美本质的新维度,并使其心性自由地随精神的解放和生命意识的流动在黑白的书法世界中不断展开和美化。
注释:
(1)借用现代美学家克乃夫·贝尔等人的观点。汉字最初以象形字为基础。它和拼音文字相比,最大的特点便是可以直接表意。后来为了方便使用,经过多次简化最后成为抽象的符号,多数已不再具有象形的意义。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线条组合,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2)转引自熊秉明《书法与中国文化》,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3)二语皆出自于孙过庭《书谱序》。
(4)见项穆《书法雅言》。
(5)见张怀灌《书议》。
(6)(7)海伦·萝斯蒂兹《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转引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8)《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9)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上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0)桂雍《汉字书法虚实演变的纵向考察》,《中国书法》1996年第2期。
(11)熊玉鹏《笔墨颂:论中国书法走向世界》,《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12)扬雄《法言》,转引自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页
(1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14)转引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5)王羲之《兰亭集序》,转引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卷第62页。
(16)(17)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l03页。
(18)见宗炳《画山水序》。
(19)见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20)熊秉明《书法与中国文化》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1)黄庭坚《论书》
(22)(23)王连升、赫志达、周德丰《中国文化要议》,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第211页。
(24)(25)转引自向春阶、张耀南、陈金芳:《酒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70页。
(26)见王羲之《书论》。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