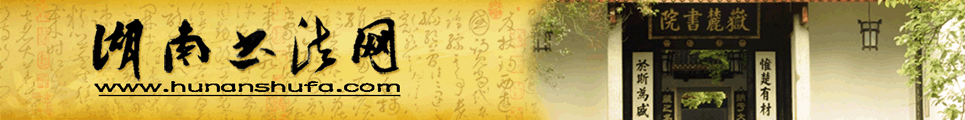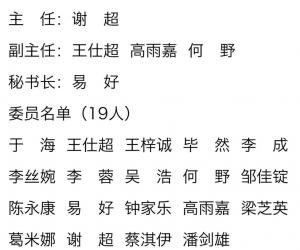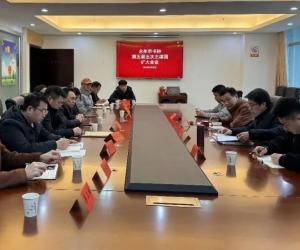尴尬——当代书法不可回避的问题 李 哲
尴尬——当代书法
不可回避的问题
李 哲
书法,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条件下产生的,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依存的。当代,我们将它成立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许多学院已招收了博士生,研究生等。书法好象是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阶段。可以说,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书法独立、纯粹的艺术性都没有被提得如此之高。而辉煌背后,是创作与理论的缺失,不能与其位并进。加上我们在认识和心理上的准备不足,从而使我们面对太多的尴尬。这些尴尬成为当代书法界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绝不可以漠视。因为它关系着书法和每一个书法工作者的前途和命运。解决好了,可以发扬光大之;解决不好,其前途无疑将是灰暗的。为此,笔者试作简要论述,以效抛砖引玉:
尴尬之一:传统与创新的难解之结
一个美术副教授,曾在一个书友的书展座谈会上不具体针对、战略性地提出一个问题:一些书法作者花一定的时间学王铎、米芾等古人,然后就可以“王”字或“米”字堂而皇之地在国展中入展、获奖,这在美术界是无法想象的,任何一个画家将历代的任何一个大师学好,即使能做到以假乱真,断没有入选国展的机会,甚至入选省、市展都很难。这番话,使我为书法面红耳热,这无疑是值得书法界深深思考的。对于在书法“围城”中苦闷者,不知是否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猛然醒悟。
其实,这位副教授说的是艺术要有创造力。这并不新鲜。艺界早有诸如“面壁十年图破壁”“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之类的忠诚。只是书法界的保守思想是如此的强烈,而创新能力又是如此的薄弱。翻开历届全国书展的作品集,就可以听到两种声音:晋、唐等古代的书法家的骷髅在笑得发颤,而当代以书法自矜,却面无表情的肥脸在流着干瘪的泪水。笔者的师友,湖南省书协理事、《书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
书法既然要成为艺术,创新显得如此之重要。许多有志之士做了或还在做着不懈的努力。这个“某某派”,那个“某某主义”,还有一些人的探索性之举,就是在谋图创新。他们许多的理论和作品还显得很浅薄,相对而言,也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在滴着血、绞着心、流着泪,越是远离传统其关系越是紧张。正如其他领域的创新一样,对于前行者来说,更多的是悲壮,在艰难中跋涉,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而如曾来德、白砥等少数人终不是太离经叛道,或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在探索中死去,远比抱着古人的大腿嚼冷馍要有意义。死死的守旧,从来就不是历史的动力。也正是屈原、哥伦布等不懈追求、勇于创造的人,才使人类历史闪耀文明的光辉。创新是艺术之树长青的根本,一种艺术一旦丧失了创新能力,那么她的命运就只能是去当作古董了。
我们粗陋地梳理一下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古人在劳动中创造性地发挥其抽象与形象思维能力,创造了天真烂漫的古文字。这时的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可以表达多种含义。随着文字本身的丰富和成熟,秦代以李斯的小篆一统天下,其它各国异彩纷呈的文字宝库也随之被禁、被毁。文字一旦成定格,其艺术成分和艺术空间也损失了大部分。从篆书过渡到隶书,经过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时期。站在历史的高度,相对篆书来说,隶书对它的突破是具有毁灭作用的,许多字的偏旁和结构等重要的文字要素都完全改变了,这不是“大逆不道”的随手乱画吗?从民间产生、流行,到被官方认可,其路途是艰难、漫长的。其开创之功在无意识的民间,实用是这种“无意识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且力度不弱。无意识的创新结出了美丽之果,一种崭新的书体从此光标史册。在隶书逐渐形成新的历史凝固的同时,草、楷、行等书体也与之并行或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先后登上前台,且每体中又有反叛与创新存在,如同为楷书的“颜体”、“欧体”。它们多彰显于所谓文人、士大夫社会阶层。随着新的字体登台,又对隶书的权威性提出挑战,这又是在继承中的毁灭和新生。在书体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即使是书法中被认为“千古不易”的笔法,也毫不例外地处于变化中。欹侧的笔法在篆书中是没有的,正是由王羲之等一些古人对笔法的创新,使之发扬光大,而在后来被广泛认可和应用。所以说,正是不懈的创新才成熟了书法的辉煌和博大,变是绝对的。创新是艺术的灵魂,创新是书法焕发艺术活力的源泉。“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许多文字体例创新都萌芽、发展于民间的史实,也正是促使当代一些人自觉地向民间取法的缘由所在。历史上这种有关“创造力”的有趣现象,也是一个书法艺术家要作反思和研究的地方。书法到底还有无创新的空间?空间有多大?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有创新的可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很好的研究的。
中国人的恋故情结是最重的,表现在书法上则为尤其强烈的恋古情结。在对“古典”顶礼膜拜的同时,滋生出恋古、依古情结,惟古是道,不见其余。其现实表现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追求越古越好,以古为艺术的至高境界。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因为古典的确有一座座的高峰,有难以抵抗的魅力。二是因为人固有的“贵远贱近”、“先入为主”的思想本性。三是因为书法的创新实在太难。一根很抽象的线条要玩出太多、够玄的花样,谈何容易?且一般难为人接受。四是因为从历史延续至今的书法教育。某人要学书法,肯定会被告知:照字帖练吧!很少会从美学的高度来启发初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五是因为现在对书法本质美没有很好的、有力的、为人公认的理论标准,或是标准不一、混乱。如“传统”与“流行”两个概念之争就颇有意味。这也是书法教育被动的原因。六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对创作缺乏有力的指导性。七是因为国展。将古人的作品“复印”就可以入展拿大奖,何乐而不为?笔者不是完全否定恋古情结,相反,承认这也是人的一种正常性绪,并建议学者们将“古”也作为书法的一个审美要素。但所谓“古亦是今,今亦是古”。关于书法的“古”,恐怕要更多的学者对之进行不懈的研究。是不是写繁体字就是“古”?写简化字,就是不“古”?字写得象某个古人,就是“古”?不象,则不“古”了?
在传统里淫懒的陶醉和在创新上的激进都是有害的,难以博得最广泛的认可。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呢?笔者主张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来作说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对唯“古典”是从,缺乏创新思维的书法界很重要。新作品,新理论,只产生于新思维。理论的薄弱,加至浮燥的社会现实,使书法家很难为自己找准一个定位,几度变换的“流行书风”就是一个证明。一个“新作品”只要在有关“大展”中被认可,马上会涌现出层出不穷的“泡制者”。可怜的、盲目的“追星族”在追着极少数的、靠各种花样(而且这种花样还可能是非关书法的)玩出的弄潮儿,虽然他们不一定就是书法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书法生存、发展中的悲哀。
另一方面,古人的文艺理论几被当代人尊为“经”,有惟古是论的味道。古人许多书论多“玄”言,且有许多篇章都是各执偏见。象《笔阵图》那样关于点画的朴素理论更是太少。当代书法则更需要富于前瞻性的科学理论来作指导。
尴尬之二:纯粹性的两难抉择
在学科细分的今天,书法更愿意强调自己是一种独立、纯粹的艺术形式。于是,激进者产生了忽视文字而重单纯的线条对空间进行分割的艺术思潮。他们中有的甚至抛弃可识的汉字字形,要靠单纯的线条来更集中地述说书法的“本质美”。如许多可归于被人称为“现代派”的作品。这引起很多人的恐慌:文字都不存在了,还叫书法吗?
另一方面的情形正好相反:主张书法家要“学者化”。这在某种人看来,无疑是对书法家的苛求,且削弱了书法作为一种纯粹、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力量。左右都不是,死守住王羲之的中庸之道才是最能讨好卖乖的。尴尬自然而生。
现今“国展”划定底线:准确、可识的汉字是书法的载体。问题还是随之而来,国展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错别字又成为众矢之的。在这个角度讲,要想保证汉字的准确性,实不是一件易事,没有深厚的古文字学根底和文学根底是很难做到的,恐怕是带着字典走都没办法;如此看来,一个书家真要将底线把握好了,不成专门学问家都不行。进一步说,既然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而且用的是古汉语,她表达一定的意义,自然这也成为书法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单靠抄古人诗词过活,怎不叫人感到书法的苍白无力?审美体验的各个环节是息息相关的。弘一法师的绝笔“悲欣交集”,了解其生平与完全不知其为何入的两种人去读的话,可能会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认知和结果。现今有人为了替历代一些有“历史污点”书法家“翻案”,要将书与人分开,也就是单纯强调书法的艺术性,这恐怕是割断了书法审美活动中的一个链条。又岂知那是当时道德环境中,人们给那些“家”的评价。也许它已不合今日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变化的,但不可就此割裂道、书、人三者的关系。如此下去,中国书法界不知会出现精神怎样颓废的一代。
尴尬之三:无力的我清高
当代书法比当代美术起步晚。在一定程度上说,书法是从美术那里分出来的。从现实的状态看,书法的发展也要比美术的发展要逊色。但书法家很容易排斥美术家,也许这是书法独立意识增强的表现。许多书法专业报刊开有“书家的画”、“画家的书”之类的栏目,在与美术亲近(其实是对立)的同时,好象要在作者的身份上来分出书法的高低优劣来。可笑的是,这时怎么又要“书”与“人”结合了。难道画家就不能同时是书法家吗?画家的字就一定不如书法家吗?
在美术界,这种情形要好得多,《美术报》、《美术大观》等美术报刊则坦然接受书法为大美术的范畴,美术家也完全可以坦然地承认自己画兰花、竹子等都用的是书法的笔法,而书法界却有许多人对齐白石、陆俨少、潘天寿、范曾等以画闻名的“书法家”怀有不自觉的抵触。而湖南省书协主办的《书画家》报将美术纳入进来,不啻是一个创举。
对有“同源”之说的画尚且如此,将外来思想和艺术当成洪水猛兽也就不足为奇了。其理由也很光冕堂皇:书法是中国国粹,外人不懂,外人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更是与书法相去甚运。如此看来,鲁迅当初提倡“拿来”可能是存在问题的。岂不知我国的现代史上的许多耻辱,就是由许多死死抱着“国粹”思想的人写成的。当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革为什么那样难?从一件满服的艰难变革就可以知道。总不如埋头“改革”点书法,可以不受太多拘束,康有为的书法与其书论也可以算开了一代阳刚之风。
不了解、不接触,就一味否定,恐怕也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事实证明,我国的美术、音乐、舞蹈等相关的艺术都可以借鉴一些外来的思想与技巧。如中国的人物画,适当地吸收西画法,还是可以保持中国特色和中国精神的。作为书法,恐怕不是要急于排斥外来思想与艺术,而是要以更开放的态度,了解、融会,批判性地消化、吸收更广泛的艺术营养,不管这营养来自哪里,要做到“英雄不问出处”。任何事物都一样:闭关是没有出路的。
为体现自己的出众,书法家会很避讳别人将书法说成写字,似乎写字的档次比书法的档次低许多似的。而当今多少所谓书法名家的水平,只怕与旧时的一些写字匠(抄手)相比都恐望尘莫及,这又怎不叫人怀疑书法会是多么高的艺术呢?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启功、刘炳森的书法很有个性,也为广大群众接受并喜闻乐见,然世称其为“馆阁体”,好象这就可以将别人的书法逐出高雅书艺之正门似的。何谓“馆阁体”?哪个朝代又有这样个性鲜明的“馆阁体”呢?不知那些自我清高者自己又弄出了些什么?千人一面、阴气沉沉的书风,成为当代书法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无奈。我倒想,中国多一些如启功、刘炳森之类的既有传统又有个性的书法家,中国书坛的气象会更灿烂恢宏。
生存在尴尬中,在尴尬中冲突,这就是中国当代书法。简单的两极否定与徘徊,独立性的支持缺乏,甚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都说明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时期。她需要更多的书法家能跳出“围城”,以更开阔的视野看书法,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书法,为书法作为艺术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此之前,尴尬还将继续。